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第六条规定:“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
这一规定意味着,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将“预防为主”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首要原则。理解这一设计,就需要懂得“预防为主”对于每个人在清洁、安全环境中生活的意义。
预防为主是经验总结
预防为主,是人类在遭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影响,付出惨痛的生命财产代价后进行的经验总结。
人类进入20世纪,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先后爆发了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美国多诺拉烟雾、英国伦敦烟雾、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以及日本水俣病、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米糠油中毒等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人们逐渐认识到,处理环境问题必须采取预防措施。
一方面,“污染容易治理难、破坏容易恢复难”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人为的生态环境破坏具有不可逆性,而且生态环境问题的后果不是一天形成的,其可能经历漫长的自然迁移、转化、富集等物理、化学、生物化学过程,也会因为生态系统本身发生空间转换,形成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复杂状态。
由此可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直接影响当代人及其子孙后代的健康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从源头开始采取预防措施,尽可能减少或避免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
预防包括双重含义
一般意义上讲,预防是指在预测人为活动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或增加不良影响的前提下所采取的事先防范措施,以防止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或扩大,或把不可能避免的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两种:
一是对环境损害的预防,即针对科学上已经确认因果关系的生态环境威胁采取的事先预防措施,以防止环境危害的产生。对于已知即将到来的损害,法律上可以通过制定规划、标准和采取技术手段防止其发生。比如,设定二氧化硫排放标准防控酸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进行环评影响评价等。
二是对环境风险的防范,也被称为预警,即针对科学不确定性风险,或者说虽然缺乏充分证据但存在重大威胁可能时所应当采取的预防措施。风险预防本质上是对“不可知”的未来采取的措施,因此需要同时具备一定的适用前提。比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是世界上达成共识的当代生态环境风险,需要在法律上采取相应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为生态环境安全设置边界,禁止或限制人类的相关活动等。
“损害预防”和“风险防范”共同构成了“预防为主”原则的核心内容。“风险防范”是适应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发展需要而对“损害预防”内涵的拓展与丰富。之所以在法律上对两者进行区分,是因为制度设计所需的理念不同。
传统的损害预防理念认为,只要科学未能证明的,就应该假定“生态环境是安全的”,科学不确定性可以成为不要求相关主体采取预防措施的理由,无需在法律上设定主体义务或责任,但是如果等到科学确认因果关系后再采取措施就已无力回天。因此,面对科学不确定性,最为关键的不是采取预防措施的必要性,而是采取预防措施的时间。即使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只要有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环境损害的威胁存在,也必须采取防范措施。这是将传统的“损害预防”拓展至“风险防范”的核心所在。
内涵扩展至风险防范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是在现行生态环境立法基础上进行的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草案第六条的规定是系统总结我国已有立法经验和实践探索的成果。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之初,就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基本方针。自1979年制定环境保护法(试行)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都确立了预防原则的重要地位。尤其是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了“预防为主”原则,反映了生态环境保护预防优先于补救的显著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相关立法已经开始出现风险预防制度。环境保护法第一条将“保障公众健康”作为立法目的,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这是法律中首次出现的“风险”概念,确立了国家的环境与健康风险预防义务。此外,土壤污染防治法设立了“风险管控与修复”专章,生物安全法就“防范和应对生物安全风险”进行专门立法。这些都表明,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的“预防”内涵已经从传统的“损害预防”拓展到“风险防范”,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确立“预防为主”原则奠定了基础。
中国进入新时代,生态安全已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草案在总结已有立法实践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不仅将“预防为主”确立为基本原则,而且通过体系化设计,使其成为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核心工具。一方面,通过建立“防患于未然”损害预防的制度体系,降低社会总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益。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未雨绸缪”的风险防范制度体系,避免生态环境风险升级为生存危机或社会风险。
目前,也有意见提出,将草案中的“预防为主”原则改为“环境不倒退”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预防为主”原则会进一步得到完善,其环境治理从“末端应对”转向“主动防控”的核心理念不能变;其平衡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通过风险防控守住生态安全底线的功能不能变;以系统性、前瞻性制度设计应对复杂环境风险挑战的制度逻辑不能变;将人类活动置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之下,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实现代际公平的价值追求不能变。
吕忠梅(作者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本报记者朱宁宁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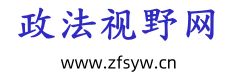




头条阅读